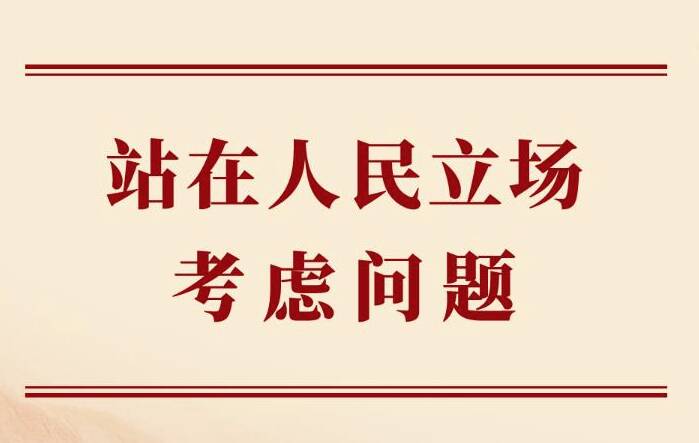从聚光灯下到车床之间,从艺术殿堂到工业腹地,半年前,吴昊霖——这位国际标准舞专业的毕业生,完成了一次出人意料的“转场”。当从学校踏入加工车间的那一刻,他携带的不是失落,而是一个移动的舞台。
在这里,钢铁是他的观众,车床是他的舞伴,他用行动诠释:真正的梦想,从不挑剔土壤。在他身上,梦想与现实并非二元对立,而是奏响了一曲和谐的双人舞。“现在这个工作就是我自己想做的,舞蹈也是我所热爱的,不用担心职业和专业不匹配,无限尝试,选择更多。”吴昊霖说。

吴昊霖正在车间工作
心中有音乐,工厂成舞台
广东佛山,加工厂内。午休铃声响起不久,在整齐列队的机床方阵之间,一片难得的空地上,一个清瘦的身影开始流动。他就是吴昊霖,24岁,这家机加工厂的新晋学徒。此刻,他正沉浸于一段无声的旋律,身体舒展,舞步精准而富有情感——那是深入骨髓的国际标准舞训练留下的印记。
没有华服,没有伴奏,没有掌声。唯一的观众,是那些在休息时分沉默不语的钢铁巨兽,偶尔有几位倚着门框、面带善意微笑的工友。这短暂的几分钟,是吴昊霖为自己开辟的“移动舞台”,也是这个年轻人用行动写下的、最生动的青春注脚:生活予我以钢铁,我报生活以舞蹈。
今年6月,吴昊霖从郑州工商学院舞蹈专业毕业。像许多艺考生一样,他曾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练功房。在毕业季的十字路口,身边的同学大多选择考研、进入培训机构,或追逐体制内的稳定。而他,这个来自河南漯河的年轻人,在经过一番现实权衡与内心探索后,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,目的地是“中国制造业重镇”——佛山。

热爱舞蹈的吴昊霖
专业与职业错位,有落差也有释然
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?”
面对这个问题,吴昊霖语气坚定,思路清晰。“以我目前的舞蹈水平,想从事这一行的话,可能就是一个变相的舞蹈销售,工资也不是很高。在工厂掌握了加工技术以后,每月应该能挣一万多元。另一方面,学舞蹈本花费高,我的家庭条件不足以支撑我在舞蹈上有更高的造诣。”
于是,他毅然“转场”,不是为了告别,而是为了以一种更接地气的方式,开启人生的“第二幕”。工厂学徒的生活,是具体的。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,与钢铁、图纸和游标卡尺为伴。学习工件精加工,要求分毫不差的精准,一如舞蹈中对于每个动作角度、力度和节奏的极致追求。
工厂里的同事,多是四五十岁的老师傅。起初,他们对这个“文弱”的大学生投来怀疑的目光。“能吃苦吗?”“不是来体验生活的吧?”吴昊霖没有辩解,他只是默默地看,认真地学,重活脏活抢着干。汗水,是最好的语言。渐渐地,质疑变成了认可,疏离变成了接纳。
“初来时,确实有落差感。”吴昊霖坦言,“特别是夜班疲惫时,刷到同龄人在世界各地旅游、在光鲜场合工作的视频,那种反差很真实。”他把这种专业与职业的错位发到网上,没想到引来了很多网友共鸣,但这种情绪并未困住他太久。
“投入到工作中,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”,吴昊霖越发明白,不要把艺术或爱好仅仅视为谋生工具,那会让它变得沉重,把它当作上天赐予的礼物,一份用来取悦自己、照亮平凡生活的礼物。只要你不放弃它,它就永远是你最独特的底色。于是,他将舞蹈视为“取悦自己的私藏爱好”,车间空地、宿舍走廊,都成了他的即兴舞台。

吴昊霖的工作日常
“人生不该只有一种跳法”
而吴昊霖的未来规划,也如同精心编排的舞蹈:短期目标,深耕加工技术,打好现实基础;中期愿景,掌握英语,打开国际视野;长期梦想:将艺术审美与工业技术融合,创造独特价值。
“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?”他认为,舞蹈生可以成为优秀的技工,技工也可以拥有艺术家的灵魂。“人生不该只有一种跳法。”
尽管,现实的挑战依然具体。目前还是学徒的他月薪不到四千元,扣除基本开销,存款增长缓慢。他与同样学舞蹈的女友身处异地,忙碌的工作使得沟通时间被压缩,感情面临考验。“但我想就趁年轻多去闯闯,多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还年轻,有试错的成本,有手艺,会技术,未来选择就会更多。”
人生是旷野,不是单行道,在每一个当下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,这就是对青春最好的致敬。“一定要勇敢迈出第一步,从0到1的突破,远比从1到10更重要。”吴昊霖说。